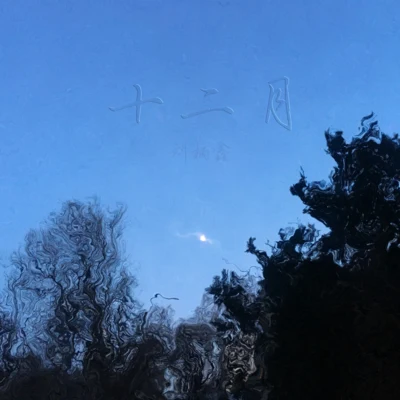還是我
 劉柄鑫
劉柄鑫
還是我 歌詞
目睹著光暗下的身影開始拉長
周圍的灼燒感在皮膚逐漸加強
驅趕的目光選擇浮躁的沉默和我發盲
歷經著風與日的洗禮直到最後成了砂糖
那是甜的在每個人的眼裡
他們把我的名字和心裡全部都寫成簡筆
可我是一艘潛艇所有人都只看到前體
當我暫時喑啞沒人把我和我連起
早就不敢看清當下的世風
有我獨處的房間我就能夠無師自通
黯然的眼睛裡剩下最後的相信
那是留給我最後的愛治愈著傷病
多難熬的時光都熬了過去
褪下的一身的疲倦就開始坐定
但仍舊害怕驚雷把我再次驚醒
一切彷彿都沒有發生過還困在冰井
端坐在檯燈下冰冷的般若波羅蜜
對照著筆劃再臨摹著波折的過去
這是二十一個凌晨等這鋼筆落地
刻製這時期的銘文整個將你唾棄
手握著燃燒的權杖去敲打黎明
腳踏著轉動的車輪準備好騎行
哪裡的花最可笑哪裡的路最難走
哪裡的生是死去有著荒誕的傳統
原來我憎恨自己像月亮憎恨著下雨
像破碎的柴火在寒冷裡害怕架起
無私是被迫消費著內心的脆弱
這秋末塵埃未落收穫承載對錯
只有得才能判定嘛失道者寡助
答案是殘酷的扼殺超脫在哪處
也不願假裝著善意只是想灑脫
只是胸無點墨自暴自棄的馬夫
你會在哪裡等我或是不告而別
會在石堆裡抵抗向我敢與山絕
知道世間匱乏包容謊言是刀鋒
孤膽的衝動已經能夠敲響這喪鐘
會以哪種方式離去的理所應當
才能悄無聲息的消失不再心傷
或許一切都只是我在自食其果
湮滅在十月的下旬冒著大雨起火
也許每個人都被既定了漫漫長路
可我不甘於不安於晝夜的往復
失敗的筆者用力的刻畫這些姓名
只有沉默是永恆悄無聲息的進行
看不清年輕的臉幕布里全心的演
我沒有面具沒有淡妝只有淚痕的繭
在每一天坦途的道上我苦痛萬千
原以為抓住了天卻只有我這半邊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念和我不同
都嚮往詩和遠方而我卻只躲在樹叢
不同的軌跡怎麼會有相交的線
沒有時間去揪扯緣分又怎會出現
都說我病得不輕我是在應病與藥
用痛苦去恐嚇痛苦遺留下無限沮喪
時間的長度超過了我的眼睛耳朵
超過了深夜里疾馳而過的每輛火車
碾壓著秋風懲罰著秋葉不留痕跡
對酒當空的歌聲環繞身體請你迴避
不必全懂得不必去言說不必穿梭
地球的每個角落追趕虛無的光波
成群的羊馬踏著雲朵離開了日出
到達了日落的落腳處豪飲著露珠
一定會有孤傲的靈魂更不可一世
可惜我無福再見就當我離世
這世間有多少的話能去與他人言說
每一筆一劃在平靜的心裡泛起連波
從長亭的燈趕到長鳴的鐘
不畏八苦八難的只有最長情的風
可突來的雨是否是因故
澆滅了燎原之火差點被吵鬧聲傾覆
幸好還剩下最後一根長燃的蠟燭
照亮了最後一片柔軟甚至昏暗的心木
相比較絲毫不暗濁不心懂
被遺棄在角落的歌也本沒想過要聽首
依然石投大海敲擊著心痛
寫過最黯然的詩是我一個人在聽誦
向無底洞裡拋出橄欖枝也沒有回報
如同兒時樂在其中的在沙海裡垂釣
即使是流沙泥海也能自顧自的穩坐
當世界開始吵雜我就被時光所冷落
這世界好像變了所有人都不想變
因為慾念的膨脹所以本心變得低廉
身處著苦海高呼著初心不變
而我只能浮躁的等到福音出現
見過指鹿為馬的人逐漸都聚沙成塔
曾抗爭的敗兵如今也都去下藤甲
任風吹雨打招來雷鳴電閃
就算是天不再亮也不能讓生命變短
那就在沉默里爆發在喧囂裡入定
生來的悟性在明天日出時復命
可誰能阻止這一切無常又無情
搭建的海市蜃樓原來看不到雛形
所以找尋存在又遺失的片段
大於此刻質疑的瀰漫低沉的呢喃
誰也躲不了輪迴的圈套氛圍的凌寒
不甘於但安於順遂和平凡
它還是喋喋不休令人無比作嘔
而真理束手無策的只能呵斥它住手
究竟誰躲在窗戶外窺探每一秒鐘
渴望膨脹追求下作的暗箭元兇
公正的審判者在哪典當著靈魂
八號當舖收割了太多無神的行人
慕名的紙張被裝在紙箱的碎片
早就注定了吧所有的高低和貴賤
有色的糖紙包裹著黃金和鑽石墜
貪念裡的堅定比鑽石堅硬三十倍
窮鄉僻壤的犬吠叫不回你的背影
失望的摘下頭冠在大風裡墜井
多希望你眼睛不再渙散嘴不再驟停
如同初見時的干淨清澈透明
流而不腐的眼淚洗刷所有灰塵
去聽到耳畔的奏鳴是你的歸程
我相信你能走很久也相信你的決心
儘管沒有人再去相信在任何時機
我知道你多麼的不堪包括你的過去
人怎能沒有幾次遺憾或者說是幸運
從往日里走出來卻發現背著罪惡
只是這外殼太堅硬所以內心太脆弱
深知再也沒有一次機會讓你再墜落
因為言語太無力所以文字更加晦澀
我沒有哪麼多的雞湯煲給你
只有滿腔的自責自咎全部交給你
總迎風飛沙的天淺嚐著黑與白的苦
在每個無言時總睡在被雨埋的土
大的失望和失落撞擊著圍牆
能讓我垂足的不過是一日頹唐
認定了往後裡不再隱藏的去向
害怕滾滾的沙塵變成滔天的巨浪
學會撤退了嗎在逆境中節節向上
還是四處招搖在風雨裡跌跌宕宕
在門外四處張望那一直在的冥頑
面對凌寒是選擇退避還是綁上行纏
久不能平復目所及的銀幕
似乎都都在演但唯獨我還不得明悟
總有一天會失望周遭被砍伐的林樹
每一次停步都只是為了再次行路
所經歷的冷眼和挫折都沒能把我擊垮
依然被自己困在低谷只是為了往上爬
每一道蜿蜒的彎都必將通向山
卻能夠眺望到目光左側的廣野和平川
也想過奔赴在人群爭渡
把大流跟住別無故分路
可哪有什麼捷徑能夠給你機會選擇
理所應當的貶責坐享其成是淺薄
街上轟鳴的車輛就快開到我房間裡
能衝出車棚的牆是否能輾碎我身體
就在這在三點二十三分的這一塊磚
書桌上唯一能夠來耀照我的那一盞燈
能夠帶走我嘛乘坐著春城的初冬
做一個溫暖不再死板的書生
路漫漫慢慢走水長流就長留
只有勇敢的獨夫才能活到盡頭
愚蠢的卑鄙者在信號裡開著車
傳來的是兩年前部隊裡唱的歌
如果說沉默能夠演變成隔閡
那肯定某一天我也就不願再沉默
多想時光暫停或者能倒退快進
朝著所想的夢一步一步的邁進
當所有的一切都比自己更加的在意
我會義無反顧的去治好這一種怪病
喉嚨裡放著仙人球我點著火
天馬上就亮了我即將無處可躲
向防盜窗問路它卻閉口不答
為什麼這麼冷漠為什麼不願說話
你也會哭泣吧哼那我不會
冰冷的金屬也會被鏽蝕也會疲憊
也許你的狀態和我一樣無比深刻
********** ****
總是有突如其來的自責真讓人失望
比如我忘記了今天晚上藥物的量
可能人活著就是為了記住和忘
那也幸好我和所有人的命格一樣
總是找藉口理由為自己去詭辯
卻忘了真相遲早都會出現在水面
只是在自欺自信的先騙倒自己
不必埋怨任何人都是我咎由自取
有人質疑我的文字說我沒有技巧
還打錯我的名字說我不懂禮貌
哼假的尊重大家爭著想要
可我不屑於作假更不屑於偽造
寫的所有句段都不是為你讓你懂
只是有話想說說不類同的內容
感謝每次沮喪時能鼓勵我的朋友
很幸運我勇敢的站在了每一個風口
我狗最後都自由了
一個人藏起來讓鋒利的去自流著
河床裡散落著偏旁重新嫁接
直到周圍的森林都演變成大街
會有多少物種滅絕多少人老了
當窗戶外不再下雨筆一定倒戈
或許有一天我就再也不會寫歌
可我還是我或許會是義種解脫
不必去猜測我的性格倔強或羸弱
是孤峰上的積雪也一點都不為過
想靠近那就先徹底離開
我的話不要信也別再抱有期待
都說財富需要開採才華需要開竅
千里馬行九百你聽這怨聲載道
摘掉那些頭銜不值一提的經歷
規矩不成方圓都搶奪著那金幣誒
沒有什麼可交流
沒有能力去教授方式依然還照舊誒
整理好著裝準備好行囊挖坑埋掉
在寂靜的土地做伏筆大聲懷笑
看這里風聲太大了暴雨在下著
孤獨立交橋被淹沒了敢問誰最害怕呢
是被拽下的青絲伴帶發的
敢問三千世界能有寸土可否容得了在下呢
當再把鋼筆放下墨水染色了手指
沉默就特不像話緊鎖著我的口齒
日曆著九死一生的都是由此
蔓延到無數的角落最後匯聚在眸子
或許沒人再去在意真誠
被下放的不是念是曾經的升騰
因為懸殊的落差讓人怨念變得重
每天都做著一個被害者才會做的夢
這城市傾盆的針陰沉的分歧
試圖妄想著無的放矢的來襲來打腫我的背
這夜晚太多困猜測的問題輾轉
難眠的無力感也試圖去架空我的胃
可能背負著污點這讓人疏遠
卻只想擦乾淨自己去面對憧憬的明天
恨透了自己不能再去讓人相信
就讓沙漏去漏盡一直到死絲方盡
我說我受夠了那些忽視
就讓我自己看著自己繼續獨自
有多少的情愫能夠去傾訴
全部都疊加起來就像是一堆積木
我說我受夠了假的尊重
所寫的每一個字都不是無用
眼看無能力的人都還在被吹捧
那就去你媽去你媽的那些認同
我說我受夠了你的抬愛
真的能夠懂嘛歌詞裡的隱喻
把我的歌詞摘改像個病句
換一個方式成為了你的警句
我說我受夠了我是我
黑夜裡自顧自不假思索
或許也只有我真的才是我
你不必聽也不必懂的那個是我